2013年,东莞石碣镇。46岁的萧大放站在一间700平方米的旧厂房里,这里之前是个洗车场,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洗车液的味道。他和三个伙伴的创业之旅,就在这里起步。
这与他熟悉的场景相去甚远。几年前,他往返于美国和新加坡,为IBM的服务器硬盘产线提供技术支持。更早的时候,他在上海航天局801研究所,与一群才华横溢的同事,共同投身于国家最前沿的科研项目。

那是个“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”的年代,在理想与现实的天平上,许多同路人选择了离开,去寻找能更直接兑现价值的战场。也正是在那个时期,他远渡重洋,在IBM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上,亲眼目睹了机械臂配合视觉系统,以超越人工的精准锁紧每一颗螺丝。
“那种技术上的差距,是代际的。”他回忆道。这惊鸿一瞥,如同一颗深埋的种子,为他多年后的创业之路,埋下了最初的伏笔。
长征第一步:从“万能定制”到“标准平台”
创业初期,萧大放与几位伙伴所创立的大研自动化,主要承接非标定制设备。“每个项目都是硬仗,基本我亲自操刀,成功率很高。”他回忆,2014年,公司成功研发出年产销量突破300万的精密VCM马达绕线机,然而高光之后,很快他便触了天花板——依赖个人英雄主义,无法规模化。
他必须为公司找到一条更宽、更厚的赛道。
2015年,他决定押注工业机器人本体。在他看来,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,而是所有工业门类的“基础平台”。一个在90年代就浸淫于全球顶尖自动化产线的人,深谙其中的工艺要点与技术壁垒。
也正是在这一年,大研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证,迈出技术创新体系化的重要一步。
2016年,研发小组成立。短短一年后,第一批六轴机器人下线。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,大研机器人的首秀舞台,选在了对品质极端严苛的日本市场。
TDK、卡西欧、西铁城、京瓷、松下……八家日本巨头成了他们的首批客户。在日本电产(Nidec)的苹果产线上,大研机器人的定价,甚至比德国巨头库卡还要高出5000元人民币。
“我们敢把重复精度做到±0.02mm,并承诺它的稳定性。”萧大放说,“很多人只敢说第一层指标,但我们敢做二级指标测试——比如这个精度能持续半年、一年还是两年?这是客户看不见,但能感受到的差距。”

▲2023年国家党史馆唯一征集收藏
2017年,大研参加全国创新创业大赛,荣获东莞赛区第一名;次年,机器人产品获欧盟CE认证,打通进入国际市场的合规通道……那是大研最顺风顺水的时期。他们的机器人成规模地进入了苹果iPhone7的产线,用于组装震动马达。“一条产线19台机器人,21条线,全部来自大研。”
风暴来袭与“五子登科”
行业的黑天鹅,总在不经意间降临。
2018年前后,一场由“平价机器人”掀起的价格战,将行业拖入深渊。
“那不是竞争,是自残。”萧大放的语气带着一丝无奈和愤慨,“六轴机器人从五、六万,被拉到三万多,接着是一万八,最后甚至出现了九千多块的产品。”他剖析了那种“传销式”的商业模式:低价收单,占用资金,延迟交货,用新客户的钱填旧客户的坑,指望熬死对手后再提价。
大研被卷入漩涡。“我们原本与‘四大家族’(国外机器人巨头)形成价格梯队的,突然之间,国产阵营里有人把底线击穿了。”原有的技术迭代节奏被打乱,整个行业在“泥巴底子还没扎实”时,就被迫开始肉搏。
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,大研仍在2019年凭借技术实力,获华为指定供应商资格,并于同年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,防爆机器人亦获得国家防爆产品认证。2020年,公司再获东莞市首台(套)重大技术装备认定,成为当年工业机器人行业唯一获此认定的企业。
为了生存,也为了突围,萧大放为公司画下了一张“五子登科”的战略蓝图——以工业机器人本体为根基,向四个新兴场景拓展:医疗器械、烹饪机器人、农业机器人、特种机器人。

一场“场景革命”就此开启。
在医疗领域,他们与国家转化医学研究院合作,研发出国内首条全自动生物标记生产线,交付给上海交通大学及其附属肿瘤医院。在农业领域,团队正在攻克基于3D视觉的棉花采摘机器人,力图改变传统收割方式对棉绒品质的破坏。

而最贴近普通人生活的,是AI烹饪机器人。“厨房智能化,是家庭智能的最后一块拼图。”萧大放说。市面上大多数炒菜机在他眼中是“智商税”,因为它们没有把人彻底解放出来——“人还得守着,做完后清洗一个重达七八斤的锅具,比炒菜还累。”
大研的烹饪机器人正是瞄准这一核心痛点,实现了从投料、炒制到清洗的全流程自动化,并做到全程无油烟。家用版产品已于2024年底通过国家3C强制认证,并累计获得超过20亿元订单,合作方覆盖大型净菜配送企业、房地产前装市场,以及社区养老、学校团餐等多类场景,以技术重新定义“人间烟火”,让智能烹饪真正走入普通人的日常。
越过山丘
“我们一路连滚带爬,但也一路向前。”
回顾十二年创业路,萧大放用不讳言其中的被动与遗憾。“2017年至今,国内工业机器人领域没有一家公司IPO成功,我们也不例外。”资本的退出压力,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,时时牵动着企业的战略神经。
然而,他的视野并未囿于自身。“我们这个行业,不仅要突破‘卡脖子’的技术难题,更面临‘链不强’的产业困境。”在他看来,一个理想的产业生态,需要强有力的“链主”来牵引,实现从核心部件到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。他曾目睹一些先进地区通过高效的政企协同,定期梳理并解决企业在订单、资金和供应链上的堵点,这让他深信,“从单点突破到整体协同,是中国工业机器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。”
他的内心深处,始终有一簇不灭的星火,那是对技术本质的执着信仰。他清晰地看到,当下所有的机器人,本质上仍是“1.0版本”,深陷于上世纪60年代福特产线的逻辑。而他信念中的“2.0时代”,核心是“极低的使用门槛”和“高度智能化”。
“未来的工业机器人,不应该只有训练有素的工程师才能操作。一个产线上的普通拉长、班长,就应该能轻松地让它换产、维护。”萧大放说,“那才是下一代机器人真正的样子。”
从神舟飞船到IBM产线,从东莞的旧厂房到与国际巨头竞逐,萧大放的创业长征,是中国制造在转型升级中跋涉的一个缩影。
山丘之后,仍有山丘。
但攀登的意义,或许就在于攀登本身——他和大研,选择了一路向前。

记者手记|“好用”本身就是一种战略
步入大研自动化位于东莞的研发车间,时间仿佛被重新校准。
门外,是世界工厂轰鸣不息的节奏;门内,一台台机器人正进行着长达数百小时的持续精度测试。没有急迫的催促,只有指示灯规律地闪烁,像是在为一种不为人知的坚持计时。
采访中,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:大研的机器人出厂前,要在车间里不间断运行整整三天。而在另一些追求“快”的地方,机器人通电能动,即刻出货。
“三天,都是成本。”萧大放语气平静。
这“三天”,成了一道无声的分界线。线的一边,是追逐风口、热衷模式的喧嚣;另一边,是甘坐冷板凳、相信时间回报的沉静。
在这个被风口、估值和退出机制裹挟的时代,很少有人愿意用十二年的时间,去打磨一款“好用”的工业产品。我们见惯了烧钱换规模、补贴抢市场的故事,却几乎忘记了,有些价值,只能交给时间。
萧大放与他的团队,选择的正是这样一条路。它不通向闪电式的财富,而是在价格战的泥沼中守住品质,在无人瞩目的角落提前播种,把“±0.02毫米精度能维持多久”这样的细节,淬炼成信仰。这些投入无法写进融资简报,却悄然构筑起他们穿越周期的护城河。
在他所描绘的机器人2.0图景里,技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黑箱,而是产线班长都能轻松驾驭的工具。这种“向下兼容”的智慧,恰恰源于一种“向上攀登”的坚持——只有真正吃透技术,才能让它变得举重若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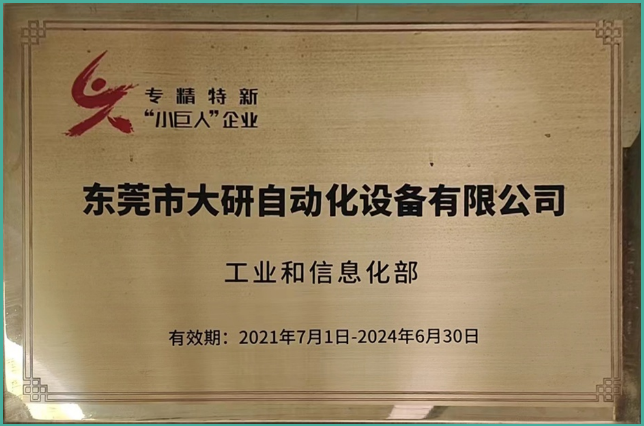
2021年,大研入选国家工信部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名录;次年,轻负载系列产品获国家科技成果奖。截至2025年,公司拥有授权专利162项,研发技术人员占比超40%……
回望那间由洗车场改造的旧厂房,朴实无华,却像一个恰切的隐喻。这让人想起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观察:“创造,是在看似贫瘠的土壤里,种下与未来的契约。”萧大放们耕种的,何尝不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中最坚硬的那片土地?
十二年间,潮起潮落,无数概念兴起又破灭。但总有些人相信,“好用”本身就是一种战略,总有人认定,技术有其内在的节奏,总有人坚持,时间终将站在认真做事的人这一边。
在这个追求速成的世界里,长期主义本身,已是最有力的回应。
文字:周子怡编辑:张叶图片:受访企业供图视频:东莞市国际技术转移中心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