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
路过街边的水果摊,看见远道而来的鲜美荔枝,不觉念起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句子,忽然就想起苏东坡来。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蜀中才子苏轼经过两个多月的漫长旅途,从汴京到西北边陲凤翔府就任大理评事签书判官,是北宋嘉祐七年春天的事,距离他被称为苏东坡,还有十九年。初到凤翔,除了一些并不繁杂的政务工作要做之外,苏轼有大把的闲暇时间随时亲近山水。然而与山清水秀的蜀中相比,眼前山秃水浊荒凉萎顿的景象让他失望透了:“吾家蜀江上,江水清如蓝。尔来走尘土,意思殊不堪。况当岐山下,风物尤可惭。有山秃如赭,有水浊如泔。”所幸在府城紧东处,发现了一泓名为“饮凤池”的清澈湖水,让他颇有心旷神怡之感,仿佛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怀抱。于是他笔锋一转,又记下自己的喜悦,“不谓郡城东,数步见湖潭。入门便清奥,恍如梦西南……新荷弄晚凉,轻棹极幽探。飘摇忘远近,偃息遗佩篸。”次年秋天,他组织劳工在古饮凤池基础上进行深凿和扩充,修筑亭台,栽花植树,并且上溯源头,引泉水至护城河从而东流入湖。正是在他的经营下,修葺一新的古饮凤池水荷交融,古柳摇曳,奇石林立,翠竹成群,曲径通幽,湖面相通,巧分为三,亭榭棋布四周,岸渚交映成趣,成了一片让人流连忘返的风景胜地,这首《东湖》诗,也因之而名传千古。
今天再看苏轼疏浚东湖,其实并非单纯为扩建游玩遣兴的娱乐场所,其中的深意还在于增强东湖的实用功能。经此一修,湖体骤然扩大并趋于完美,使东湖在作为游玩憩息之所的同时,兼具蓄水灌田的作用,这是之前他人未能为之的丰功硕德,历来广受赞誉。人生总有不可预知的机缘巧合,在凤翔修筑东湖将近三十年之后,苏轼又在杭州疏浚了西湖,两湖南北遥望,人称其为姊妹湖。西湖之水明净,东湖之柳高洁,所以有人这样赞美:“东湖暂让西湖美,西湖却知东湖先”。在东湖的荡涤下,苏轼的才华不可抑止地一发而不可收拾,这一时期创作出了近二百篇诗文,千古传唱的名篇除《喜雨亭记》外,还有《凌虚台记》《凤鸣驿记》和《思治论》,为东湖和凤翔留存了一笔丰厚悠长的文化情韵。
初到凤翔,苏轼无疑时时春风得意、处处满目青山。但很快却有一件事情,让他郁闷不已。
嘉祐八年正月陈希亮就任凤翔府知府,成为苏轼的新上司。陈希亮和苏轼性格如冰炭不相融合,加上苏轼少年得志,难免浑身傲气锋芒太露,不断产生的摩擦造成两人成见日深。苏轼是落落寡合,倍感憋屈,在许多事情上故意消极抗争,找借口不配合太守。陈希亮本是眉州青神人,和出身眉州眉山的苏轼份属同乡,比苏轼的父亲苏洵还高了一辈。他曾对别人说:“吾视苏轼犹孙子也。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,以其年少暴得大名,惧夫满而不胜也,乃不吾乐耶!”直至数年之后,苏轼才认识到陈希亮的苦心。他明白老太守是在有意裁抑他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,因而日后在为其做墓志铭的时候说:“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,而轼官于凤翔,实从公二年。方是时年少气盛,愚不更事,屡与公争议,形于言色,已而悔之。”于此充分表达了对这位长者的敬仰和感激之情。
对于苏轼的这种倔脾气,其实其父苏洵早就看到了,所以才给他取名“轼”。轼的意思是车上供人凭倚之横木,《左传》中有“凭轼而观”之语。老父苏洵希望他的长子含蓄内敛,为他人提供倚靠。他最怕的就是儿子锋芒毕露,不会藏拙。在《名二子说》一文中,他曾忧心忡忡地说:“轼乎,吾惧汝之不外饰也。”年少多才的诗人可以任性,但作为体制内的一名官员,无疑是必须含蓄内敛的。陈希亮对苏轼的苦心,可以说和苏洵如出一辙。
离开东湖之后,好运就不再一直追随,苏轼的人生之旅渐渐变得坎坷多难起来。在外放做官的二十多年里,他饱受颠沛流离不能稍事停留。
一心想要革除“财之不丰、兵之不强、吏之不择”三患的苏轼,后来一系列的遭遇,无非是给这个定律多增加一个例证而已。在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中,身陷囹圄一百多天,他遭到严刑拷问,险些丢掉性命,但依然安睡无惧。对于天性耿直的苏轼,如果没有当年在东湖之滨经受过陈希亮的“挫折教育”,遭受天大的不白之冤,他能心无芥蒂地酣睡如雷吗?
王安石曾经无限真诚地叹惋:“不知更几百年,方有此人物!”作为历史中绝版的传奇,苏轼确然难以再现,那些和苏轼生在同一时代的人们,能够亲自感受他光风霁月的人格魅力,实在是有福了!苏轼留下如此众多的诗词文章,今天人们能够吟诵行云流水的苏氏诗文,感受生命的欢愉和高贵,实在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,生在苏轼之后的人们,同样有福了!为东湖题写过大门楹联的清乾隆朝状元陕西巡抚毕沅,就是“苏粉”中的超级铁杆粉丝,每到阴历十二月十九苏轼生日,他会专门腾出功夫,中堂悬挂苏轼肖像真迹,两厢下排列数以百十计的艺人笛箫演奏其自作的“迎神”“送神”曲,亲率幕僚、门生和当时有名的文人骚客冠戴整齐拜谒苏轼遗像,随后大宴来宾,即席赋诗唱和,是当时人人称道的文坛盛事。苏轼在后人心中的地位和重量,可见一斑。
有了东湖的粼粼波光对苏轼的浸润和沉淀,不管后来政治上的打击怎样接踵而来,他都能始终如一地快乐着,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地享受短暂的生之乐趣。今天我们在苏轼的诗词文赋中找不到一丝丝的怨悔,更多看到的是“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旷达,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通脱。林语堂说苏轼是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,可谓一语中的。苏轼骨子里的那种潇洒和超脱,代表了古代文人生命的最高境界,不管遭际如何,都能珍惜每一刻时光,从不曾顾影自怜,怨天尤人,把生命白白浪费。苏轼这种乐观、旷达的人生态度,千年之后更加叫人感动,值得每个人终身练习!
每次到东湖,站在环湖路上,我都会吟咏一遍《东湖》诗,心中由此洋溢着一种暖暖的情韵。我若有幸生在北宋,说不定也可以遇见这位大文豪呢。昔日郑板桥仰慕徐渭,曾自制一枚刻章自称:青藤门下走狗。真要生在北宋,我也愿作苏轼面前一头牛、一条狗,或者一只猫!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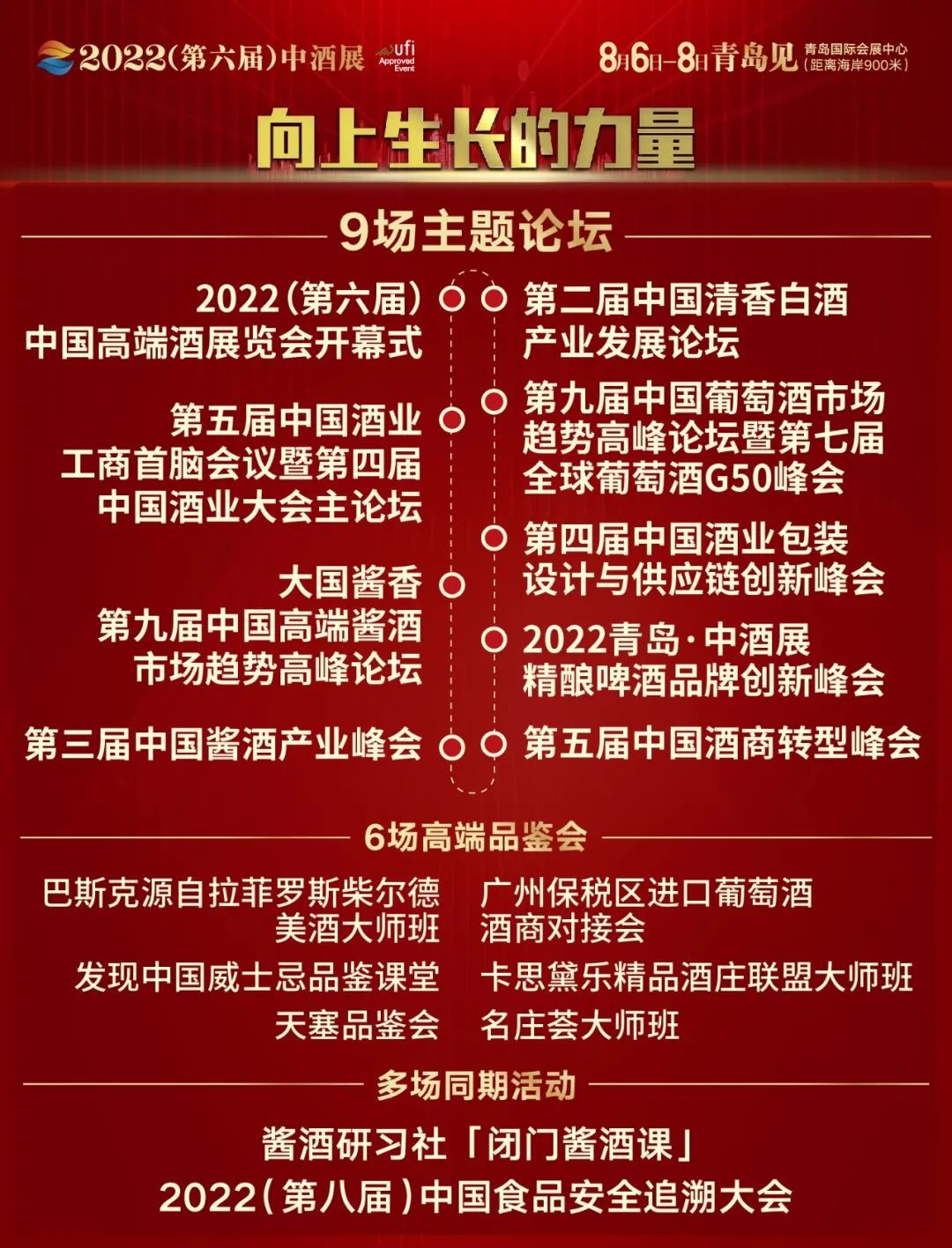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![视焦点讯!(图表·漫画)[经济]加强抽检力度](http://imgs.hnmdtv.com/2022/0610/20220610024400214.jpg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